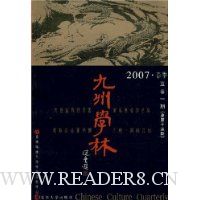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页码:348 页
出版日期:2008年07月
ISBN:7309045300
条形码:9787309045307
版本:第2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Pages Per Sheet/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本书为九州学林2005春季(五卷一期)(总第七期)内容有论文,考释,论坛,书评等。
目录
论文
冯国栋 宋代文人与《景德传灯录》
黄启江 论宋代士人的手写佛经(下)
彭国翔 杨时《三经义辨》考论
陈以爱 胡适的《水经注》藏本的播迁流散(下)
考释
许子滨 敦煌《占云气书》残卷与云雷兴象
林悟殊 摩尼教华名辨异
张颂之 对王国维书信日期的订正——附罗振玉有关书信的订正
论坛
张伟然 《行历抄校注》商疑——特别是关于入唐留学僧圆载的史实
书评
冯志弘 唐宋文化转型的个案研究——评杨国安《宋代韩学研究》
……
文摘 杨时《三经义辨》考论彭国翔
一、引言
余英时先生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中有一个重要论点,即指出:就儒家士大夫必须“得君行道”而经世致用,以及经世致用的“外王”实践必须建立在“内圣”之学的基础之上这两点而言,王安石的新学和两宋的道学群体是一致的。或者说,在这两点上,其实可以说道学群体继承了王安石的精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余先生说:“我必须郑重指出:强调‘外王’必须具备‘内圣’的精神基础是王安石对宋代儒家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在这一特殊论点上,也可以说他是宋代最先接上孔、孟旧统的儒者。”①至于道学家群体对于王安石的批评,根本并不在于王安石“得君行道”的政治取向本身,而在于在他们看来,王安石的“外王”实践建立在错误的“内圣”之学的基础之上。正因为这一点,余先生引《二程遗书》以及《二程萃言》中的材料,指出北宋时代以二程及其门人为主的道学群体将王安石的新学视为首要的思想敌人。并且,余先生还引《二程遗书》中伊川的话以及《朱子语类》中朱熹的话,指出明道与其高弟杨时(1053——1135,称龟山先生)曾经共同钻研过王安石的著作。从余先生征引的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杨时应当是当时道学群体批判王安石新学的重要代表。用伊川和朱子的话分别来说,即“杨时于新学极精”、“龟山长于攻王氏”。余先生引用朱子的材料如下:
《龟山集》中有《政日录》数段,却好。盖龟山长于攻王氏。然《三经义辨》中亦有不必辨者,却有当辨而不曾辨者。(《语类》卷130《本朝四》)在征引这段话后,余先生紧接着说:
《政日录》当即《神宗日录》,《三经义辨》则集中未见(我用的是《四库》本),恐已散佚,俟再考。②既然《三经义辨》是杨时从“内圣”之学的角度批评王安石新学的文字,那么,对于余先生书中未及考证的《三经义辨》,笔者不由萌生了了解的兴趣。以下是初步的考证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其相关意义的观察,希望得到余先生以及其他有兴趣的研究者的指正。
后记 一般而言,学术研究是知识的纯粹钻研,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凡是我不知道的,别人弄不清楚的,过去学者探究未尽的,都是学术钻研的领域。做学问,是心灵的探险,是超越功利的知性追求,是不求闻达的自我升华。
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心目中的“古之学者”,大概有这种纯粹的心境,遗世独立,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道德修养,不为外界名利诱惑。不过,本来是纯粹知识的探求,是对外在世界的认知,对宇宙自然、天文地理、草木鸟兽的“格物致知”,在孔老夫子那里,突然“天人合一”了,转化为内外兼修,变成“内圣外王”的修炼过程。我不由得想起王阳明“格竹子”的心路历程:一开始是外在世界的研究,把竹子当作客观的物体来“格”,格来格去格不出名堂,格到精疲力竭,完全崩溃,终于放弃。这种由客观外界攻关的研究法,转而寻求内在认知的圣贤之道。他不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下手,不走发明放大镜、显微镜、细胞切片、基因分析这类实验工作的途径,而企图通过“天人合一”的捷径,把客观知识的探求转化成自己内在认知的心理过程,也不知是展现了中国文化思维的“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