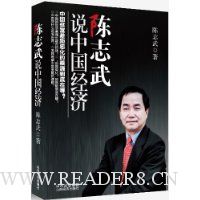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山西经济出版社
页码:267 页
出版日期:2010年01月
ISBN:9787807672524
条形码:9787807672524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
正文语种:中文
外文书名:Chen Zhiwu's Comments On China's Economy
图书品牌:北京磨铁文化
内容简介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到底在哪?怎样理解中国金融的逻辑?“新国有化”的危险到底在哪?”陈志武为民代言,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今天,他试图用理性解决这个时代的焦虑,他的金融思想诠释了给人幸福是一切学问的基点,在一般人看来很严肃的名词——制度、分配、股权……都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具体工具。本书聚焦中国,通过对中国当前社会的分析,探讨了中国人的未来,非常明确地指出了中国的改革方向以及中国人寻求幸福的具体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民众权益的代言书,一部中国社会转型的启示录。
作者简介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
自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以来,陈志武教授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长江商学院等国内著名学术机构聘为访问教授。
陈志武教授一直是世界金融学经济学和资本市场研究领域最具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获得过美国默顿?米勒(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重大学术奖励。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教授排名第202位;2006年,《华尔街电讯》将陈志武教授评为“中国十大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
陈志武教授拥有国内经济学术界少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他也是国内鲜见的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把事情说得很清楚的经济学家。“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金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什么角色”、“金融发展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等观点启发了更多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经济的思考。
2008年出版的中文著作《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非理性亢奋》成为当年度最具影响力的财经读物之一。其中《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荣获“2008和讯华文财经图书大奖”之 “年度财经图书大奖”和“最佳原创学术类”大奖,并入选多家专业媒体评选的2008年度最值得珍藏图书。2009年出版的《金融的逻辑》已入选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 的“2009年度十大图书”。
媒体推荐 经济、哲学、宗教、科学最终是统一的,好的经济学家也是哲学家,比如索罗斯、比如陈志武!社会生活的内在价值,哲学、政治、经济都是可以贴现和比较的。真正大师的功力表现在能用很浅显的语言把本学科的东西说透,让一个毫无基础的初学者都能听懂,了解到学科的基本原理,甚至本质。
编辑推荐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最有影响力的华人经济学家,继超级畅销书《金融的逻辑》后最新力作,《新财富》《经济观察报》《新京报》《资本人物》《南风窗》《人民日报》《长江》《南方周末》《商务周刊》《中国企业家》《证券市场周刊》《外滩画报》《海内与海外》《新青年》《国际融资》《上海证券报》《21世纪经济报道》《嘹望东方周刊》《22度观察》《南方人物周刊》,搜狐,新浪全力推荐
专业书评 吴敬琏(经济学家):说到经济学理论,我没有办法跟那些经过严格理论训练的人比。比如钱颖一、许成钢、陈志武、白重恩等,他们常常能用现代经济学的源流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秦晖(学者):陈志武教授的著作“深入浅出,说理透彻,把财富创造的制度基础讲得很清楚”。
易宪容(经济学家):陈志武可以把很难、很深的金融学理论用很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
秋风(评论家):陈志武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在国内经济学术界是少见的,面对纷繁的现实,他不仅对其进行技术经济学的逻辑分析,还进行了法律与政治的分析,从而更为正确地解释了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
何力(资深媒体人):陈志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财富增长的制度性内涵,使我们明白,仅有个人的机遇和聪明才智是不够的,在勤劳和富有之间还有一座必须建造的桥梁——好的市场经济制度。
许小年(经济学家):改变中国目前国富民穷的状况,一方面可以减税。另一方面,就是陈志武教授所讲的,要改变资产配置,我非常赞成中央在“十七大”提的口号,就是增加居民的资产性收入。
张维迎(经济学家):应将国有企业股票一部分分给老百姓。陈志武等人曾提出过类似建议,我很赞成。
苏小和(财经作家):有陈志武在,我们的经济学视野就会持续开阔。
目录
目录
序言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 1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
谁是陈志武 /
生活经历与观点自述 /
一个学者的幸福与思考 /
第Ⅰ篇“中国奇迹”背后
改革开放30年的启示 /
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能否持续 /
香港繁荣之路 /
制度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 /
官僚体制不利于科技进步 /
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 /
第Ⅱ篇国富民穷之忧
“新国有化”的危险 /
宏观调控与国进民退 /
走出产权改革的误区 /
呼唤13亿百姓的国民权益基金 /
拿什么保护农民权益 /
中国贫富差距恶化的根源 /
第Ⅲ篇金融市场变革
国有金融体系加剧了经济不平衡 /
中国股市乱象 /
大陆与海外股市的差别 /
机构投资者如何发育壮大 /
冷眼旁观基金法 /
理解金融的逻辑 /
第Ⅳ篇面向全球化
新时代的中国海外利益 /
解析中美贸易矛盾 /
外资进入中国为何受阻 /
私人股权基金对中国经济有利 /
外汇储备投资难题 /
中国凭什么走向世界 /
第Ⅴ篇从危机到黎明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影响 /
我们怎样度过这场危机 /
在逆境中转型 /
以减税、退税提振中国经济 /
四万亿如何救市 /
危机对中国的正面机遇超过负面 /
中国可能是“金融海啸”的最大赢家 /
尾声
一位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情感 /
制度决定幸福
……
序言 序言
中国是世界进程的一部分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如何理解中国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尤其是30年来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是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福山教授的著作《历史的终结》引发过一场大讨论,那场讨论至今在中国还在继续。对“中国奇迹”,一种解读是,这是信奉大政府主义和“中国特色”的结果,由于政府独享强制力,利用强制力调配资源,高效率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才成为可能;另一种解读则恰恰相反:这些成就与其说是强制力配置资源的结果,是“中国特色”的奇迹,还不如说是自由市场、普世人性战胜权力管制的结果,是全球化力量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的成就佐证了自由选择和市场化会带来繁荣,并且这一结论跟人种、肤色、文化传统无关: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被解放得越多,权力对权利的束缚被结束得越快,老百姓的经济福利就增长得越多。
按照福山教授的说法,人类社会在制度体系上的演进,最终以“自由民主加市场经济”而结束,自由市场解决物质需要问题,自由、平等、民主不仅能保障市场经济,而且能解决人的非物质需求问题,所以,虽然社会与个人的生活还会继续颠簸,高潮性的喜剧和悲剧仍将重叠发生,但人类漫长的“大制度”——大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架构——追寻历程到此为止了,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搭配。
福山理论的对错,可以留给每个人自己去思考评判。但对中国的许多学者和业余知识者来说,可能首先无法接受的是福山将所有社会——不管人种、政治文化背景——都放在一起谈,好像没有白种人、黄种人、黑人的区分似的!尽管被我们的社会定位为“圣经”的马克思主义也来自西方,但在很多人看来,似乎中国历来就不同,西方的东西不适合中国,任何不针对“中国特色”加以区分的理论,当即就该被贴上“盲目照搬”的标签。
在别国行得通的,真的拿到中国就不灵;在中国行得通的,到别国就水土不服。真的如此吗?中国3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历是支持还是颠覆了福山的思维框架;是证明还是证伪了他的历史终结论?中国漫长的历程真的游离在世界历程之外,从而使中国的发展不能与其他国家一概而论吗?
一
在我看来,除了一些相对短暂的时期外,中国从来就是人类进程的一部分。以远古看,中华文化创立于2500年前的先秦,在那思想文化的鼎盛时期,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8年)、墨子(前468年~前376年)、孟子(前372年~前289年)等大师百出。
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奠基时期几乎是同时的,代表人物包括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前399)、柏拉图(前428年~前348年)、亚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等。
佛教文化体系大约起源于公元前400年的印度。而印度文化的核心——种姓制度也是在公元前2500年~3000年前发展起来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熟悉的主要文化体系差不多都是在那一时期发展起来的?难道是完全无相互关系的巧合?还是有某种必然的联系?那种必然联系是否就是人类社会从游牧走向农业,在固定地方耕种粮食,在室内圈养肉食动物呢?
文化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宗教,中国与其他国家也相当同步。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传入汉朝中国,并逐步融入中国社会,给中国人带来后生世界的秩序。基督教在同一时期出现,并渗透到欧洲社会。这说明,一方面中国对外开放的时间比以往说的要早,另一方面外来的文化也能在中国社会扎根,毕竟人性是一样的。
伊斯兰教是世界另一大宗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表面看,这比基督教进入欧洲、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晚6个世纪,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时期,或者说在中世纪商业革命、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社会变迁慢,发展速度低。根据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安德森?麦迪逊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花了1880年的时间才增加了1倍。然而,从1880年到2000年,短短120年里,全球人均GDP就增加了近5倍。也就是说,过去120年所完成的人均收入增幅,是1880年之前近2000年人类所完成的增幅的5倍。照此来理解,佛教进入中国、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伊斯兰教的出现,虽然客观上时间相差几百年,可是从人类进程速度来理解的话,大体上算是同一时期。
15世纪初期,明朝中国大举航海,不久之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也加入,积极推动海上冒险,以至于在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所以,在航海事业上,中国不仅没有偏离世界潮流,还引领人类的这些尝试,只是到后来在航海事业上退缩了。
在商业发展方面,中国与世界的同步就更加紧密了。我们知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大陆是西方商业革命的标志性时间点,之后几世纪商业革命进展迅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亦即自1500年~1800年,中国也在经历一次商业革命,那是公认的近代中国商业最鼎盛时期,或者说是此轮经济崛起之前的最鼎盛时期。
为什么中国过去的许多重要文化、宗教、经济进程与世界其他国家那么同步呢?难道每次都是巧合?如果不是巧合,那不是说明在大的事情上中国并没有与众不同,“中国特色”在历史上并非我们说的那么特殊吗?
二
在近代,中国与世界更加同步。我们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是加入工业革命的时间。1780年左右,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出现,后来蔓延到美国、法国等少数国家,德国、意大利等西欧以及东欧国家是19世纪中期才开始追英赶美,拉美、亚洲、非洲国家差不多也是在那一时期模仿英美工业技术。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中国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是同时,其核心就是要引进西方技术,在时间上当然比英美晚,但与世界多数其他国家同步。比如,电报在1837年~1844年间快速发明成功,19世纪60年代在各国普及有线电报,兴建跨国电报网,1871年电报进入中国。世界第一条火车路于1825年建于英国,50年后在中国的上海也有了第一条铁路。汽车在西方出现后不久,于1901年就进入中国。电话于1876年在美国发明,投入使用后,也很快进入中国。
以往我们责怪清政府,指责中国没有发明出各类技术,这些本身当然都有道理,因为中国毕竟是世界大国,但是,从跟随世界潮流的角度看,中国并不落后,与其他国家雷同。
第二是金融市场的发展。鸦片战争之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票市场交易等现代公司制度、现代金融于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这些企业制度、金融技术比西欧国家晚400年左右,所以,比他们落后,但是,与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同时。中国自己的第一个股份有限公司——轮船招商局于1872年上市交易,标志中国股票市场的开始。跟其他国家比落后多少呢?瑞士股市成立于1850年, 西班牙1860年, 匈牙利1864年, 土耳其 1866年,澳大利亚 1871年, 捷克1871年, 阿根廷 1872年, 新西兰1872年,加拿大1874年,巴西1877年, 印度1877年, 挪威1881年,南非1887年,埃及1890年,中国香港1890年,智利1892年,希腊1892年,墨西哥1894年,新加坡1911年。这当然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第三是政府办企业以及国有化运动。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国家资源为主,经历了“官督商办”到“官商合办”,再到纯粹“官办”,这一做法跟同时期的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没有太大差别,都想靠国家的财力追赶英美工业技术。
1918年苏联开启国有化运动,将工业、商业全面收为国有,将土地收为公有。20世纪30年代开始,前苏联经济快速增长。与此相对比,1929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引发了西方私有经济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苏联国有经济的高增长,跟西方私有经济的大危机,反差如此之大,使世界各国普遍学习国有化,也由政府办企业。中国先是在20世纪30年代小范围内做国有化,到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国有化。东欧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有化。亚非拉美等许多国家都跟踪模仿。连当年的私有制西欧国家也在一些行业进行国有化,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以及之后陆续将煤电、广播、铁路、钢铁、油气、公交等行业国有化;法国从1938年开始,将主要银行、金融、油气、汽车制造企业国有化。所以,中国的国有化以及相关政府权力扩张,并非中国的孤立行动,而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当然,中国的国有化运动与世界同步,后来的市场化改革也与世界同步。中国是因为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经济局面每况愈下,“文化大革命”期间将经济进一步推到低谷,以至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计划经济不结束不再可行了,所以,就有了1978年启动的改革开放。其他国家虽然没有中国“文化大革命”那样极端的经历,但是,国有企业、政府管制经济也给他们带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英国到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拉美国家、东欧国家、亚洲国家、非洲国家,全球范围都被迫进行私有化、市场化改革。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中国跟其他国家在远古时期基本同步,在近代同步,中国历来是世界进程中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人跟世界其他人一样,都有相同的人性,追求美好生活和个人自由的人性。所以,我们可以就福山教授的结论进行商榷,但是不应该以“中国特色”,要求将中国放在对人类社会未来走向的预测之外。
三
从1978年~1998年之内的短短20年间,中国人均GDP翻了两倍多,中国历史上当然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奇迹。可是,如果我们看到,世界人均GDP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才翻了1倍,但从1880年~1978年间,却翻了3倍多,在那100年间中国人均GDP只翻了一倍,这等于说,工业革命带给中国的发展机会被留给了1978年以后。这样,我们就能知道改革开放30年间快速发展的主因了。
首先,我们看到,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包括两个内容,“改革”主要是相对政府资源垄断、政府管制而言,指的是恢复个人的自由选择权,让老百姓有权利决定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如何做,做成的东西卖多少、到哪里卖、以什么价格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开放”实质上也是扩大自由,是让中国人和外国人能更加自由地进出国界,做投资,做贸易,让个人经济自由权跨越国界延伸,拓宽自由的地理边界。所以,“改革”与“开放”都是围绕“自由”,是放开约束。
简单地把老百姓手脚放开,释放人要生存、要过更好日子的本性,这就是中国过去30年方方面面新政策的主旋律,也恰恰因为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等在中国门口数十年的全球化力量也能进入中国,让中国社会终于能尽情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简单地释放自由就能带来经济繁荣,如此之快地提高生活水平,这当然是奇迹,但这是“自由”的奇迹,不是“大政府主义”的奇迹。
从逻辑上和时间序列上讲,如果“大政府主义”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那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不是更有可能出现经济腾飞吗?实际的情况是,正是由于“大政府主义”在六七十年代造成的经济灾难,才为1978年开始的自由市场化改革提供了政治动力基础。而且,在那之后,经济自由恢复得越多,经济就增长得越多。
因此,改革开放的成就验证了“自由促进发展”的道理,中国的经历没有偏离其他国家的实践所证明的规律。适合其他国家的制度也照样适合于中国,人性是没有东方西方之分,也没有中国人和外国人之分。
梳理中国的事,我们必须避免只用中国以往的套路,不能以“中国特色”为由回避实质性问题。离开世界文明、离开人类社会的变迁经历,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经历,也更难为中国的长久持续发展提供建设性视角。
四
这本书收集了笔者过去几年的一些媒体专访,内容涉及不少话题,但基本都围绕中国。即使谈到世界、谈到其他国家,最终也是为了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为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是用中国的过去理解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那只会得出片面,甚至错位的结论。只有参照同期或者早期其他国家的经历,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中国,预测我们的未来。
这些年,许多媒体朋友给了我向大众表达观点的机会,在此表示感谢,特别是岑科、李利明、郭宇宽、周年洋、赵灵敏、刘凌云、笑蜀、何雪峰等人;也特别感谢本书所录文章的其他作者朋友,包括刘浪、郭哲、唐勇、李翔、叶筱静、钟加勇、许凯、魏、周程、陈竹、石贝贝、谷重庆、周慧兰、曹理达、李静睿、郝希良、肖强、叶檀、朱周良、徐琳玲、谢文思、王利芬等,没有他(她)们的采访,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现。岑科负责收集整理本书的文章,他的贡献自不用说编注:本书收录的文章大多通过媒渠道收集,书中标明的发表日期可能与刊物正式发表的日期有出入,有些文章的标题和内容有改动。。愿书中的所谈所指,能给关注中国社会发展的读者带去启发和思考。
2009年9月25日,于耶鲁大学
文摘 在中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约有6000人,但能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经济学者只有大约100人,陈志武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2006年2月,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上榜的10位经济学家中,陈志武教授名列其中。
一
问:中国的老百姓都觉得经济学家是高深莫测的,包括您今天坐在我对面之前,我都一直在心里面描摹您神奇的模样,您平时的生活跟普通老百姓有区别吗?
陈志武:没区别,我从来也不觉得我不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普通老百姓,家庭背景很一般。我没有权力,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做一些学术研究。我觉得,做学术研究的人能够像一个普通人那样去体验生活,感受社会,对人和社会的研究才会更确切、更扎实;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有各个方面的情感,有各个方面的欲望,才是正常的。
开篇陈志武和他的思想王国陈志武说中国经济 问:可能很多人都在想,您这样一位能站在世界舞台上的经济学家,一定是出身名门,或者是书香门第,实际上您成长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呢?
陈志武:我家在农村,我从小是在湖南茶陵长大的。当然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是觉得一个人的经历要是能够丰富多彩的话,对于研究社会、研究经济、研究人、研究文化等不同学科的学者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问:您觉得您的经历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吗?
陈志武:我觉得是很丰富多彩的。当然可能这也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判断,因为要我回过头来看的话,从小在农村长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开始每天要下地劳动,或者是上山砍柴,因为我们湖南的农村,尤其是那个时候,不烧煤,也不烧别的,就是烧木柴,所以一直到我高中毕业,也就是1978年、1979年,差不多只要一有时间,一回到家,要么是下地干活,要么是上山砍柴。当然也正因为这一点,在我1986年去美国以后,就去耶鲁读书,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这些年的变化还真是蛮大的。
现在想起来有一点很后怕,因为当时确确实实有许多事情不知道。我报考耶鲁的时候,选的是金融学科,我说这个金融是什么?在连任何一点基本信息也没有的情况之下,是我自己这样子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从中南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再到美国求学,从攻读计算机、系统工程再到转学金融,当年的陈志武
……
后记 一位经济学家的理性与情感
与陈志武交谈的时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不仅时长超过了我的预期,而且谈话的深入程度也是如此。
陈志武是一个看起来脚踏实地的人,平时很难从他脸上读出过多的表情,这也许是作为金融学教授长期严谨的理性思考和众多的数据模型建立的缘故吧。但这次采访我却看到了他对中国现实思考的极其丰富的情感状态。采访中间,在谈到中国由于制度建设的缺乏带给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时,他竟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流下了眼泪。在那一刻,作为一个来美国只有十多天的我来说,很难完全理解一个在美国居住工作了十多年的他,但他对中国的感情与牵挂却带给我无数多的思绪。
我在历史系选了一门与中国相关的课,在芭来特教授有关中国现代史的课上,她这样介绍着中国:一个在文明古国发明过四大样东西,且对人类文明有过贡献的中国在后来变得无声无息,然后就睡过去了,一睡就是好几百年,二十多年前,她突然醒来了。这个描述的确非常有意思,这不是一个概念性的描述,而是一个极形象且能带给人许多思考的讲述。课下坐着真正来自五湖四海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我在想,他们会从这个介绍中怎么想像中国的今天呢。
陈志武所为之激动和担心的,当然是一个长睡者之后醒来的中国状况,她的状况与其中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
陈志武来自湖南一个落后的农村,在中国上完大学和研究生后,带着几十美元到美国,在耶鲁大学完成了金融学博士学位,之后到俄亥俄大学任教,最后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过去贫寒而简陋的乡村生活和目前他富足而充实的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在他身上对比应该是无比的强烈,我也见过经受过这种强烈对比的人,在他们身上,这种两极化的体验慢慢会让一个人思考更多的问题,即使不是学者,他或她也在思考着,因为这种思考不是一般性的问题探索,而是与自己带着体温的记忆相关联。
我相信每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来自一个最深沉的动机,这个动机就像一个无形的发动机一样在驱动着每一个灵魂走着他们自己开始未必能预料的线路。
陈志武的专业是金融,但他目前所研究的领域已扩展了许多,与经济相关联的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众多的问题他都关注。在他流泪的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明白了他所关注的对象为何这么广,这个问题本来一直想问,但我想我的确明白了。近年他呼吁最多的是关于中国的制度建设,中国正在发生着真正意义上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紧跟这个变化的应该是一系制度至少是制度框架的建立,然后才是一点点地细化,要不然社会所积累的财富将无法支持持久的发展。
他从制度建度的角度对金融、农民和外贸等问题进行许多的探讨,这些问题无不带着他对中国问题的思考,有许多问题就是从一个思考着的问题中派生出来的。他目前的状态处在两个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中,每年他都多次回国,这种在多元文化的大舞台上的走动,使他的思考一直是将中国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及与许多国家对比中来完成的。其历史和地理两个角度的交叉使他的许多想法给人启示。
一
问:陈教授您好,今天上午我一直在读您的文章,在许多文章中,您呼吁最多的就是关于制度建设对于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但如何建设?能否在您所熟悉的领域中为我们举一些例子。
陈志武:我最近的文章一直在涉及这个问题,尤其在新闻领域的开放度和司法独立的问题上,过去三年来,我都在做这方面的探索。在金融领域方面,有利于市场发育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我想有很多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作为我们来说可能是将许多人没有说出来的话把它说出来了而已。作为制度建设,重要的是要从一些细部入手,从具体的方面向人们解释为什么这些制度建设很重要,而不是大而化之地让大家感觉这个就重要。为了这个问题,过去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收集了许多数据,研究这些问题。我喜欢退回到二百年前,或者三四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当初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和架构对当时经济活动的范围和经济活动的规模来讲,可能差不多够用了,像我老家湖南省的各个镇和村是不怎么来往的,但是在那个农业为主的社会里,市场交易相对来说是简单的,而且是小范围、熟人范围之内的。在那种简单的交易环境下,那些独立的正式司法或新闻媒体对经济交易都不是那么太重要,因为说到底每天打交道的都是比较熟悉的人,熟人之间有传统的道德来约束,所以有没有一个法官来帮人们调解纠纷并不是很重要,而且也因为以后世世代代都在同一村、同一地,中国社会中,熟悉的人中间是有约束的。有了这些约束后,使那个社会对正式司法和新闻媒体的需求不大。
可是,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交通和通信的发展将整个中国社会不同的地区融合成了一个整体的经济市场,这种大规模的跨地区融合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当发生了跨地区的市场交易后,出现了问题找谁?而更多的买卖是一次性的,这时候传统的道德约束就不管用了,因为现在更多的是陌生人间的跨地区交易。这时如果司法系统跟不上来就要出问题,这种交易就会受到抑制,人们就会回避跨区域的市场。这样,中国现有的交通、通信网所提供的物理性便利的潜力就不可能发挥出来。交通、通信硬件上来后,法治这种软件会不会跟上来就很重要,要不然人们会花很长时间去判断这个生意要不要去做,做起来的交易成本也会太高。所以司法的独立和对司法的可靠性的信任,将决定我们所拥有的交通和通信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这里,一个开放自由的新闻媒体的作用也很重要,它也是促进跨地区经济市场的深化的必要条件,能帮助疏通市场交易所必须的信息环境,减小作假与行骗的空间。
问:您刚才所讲,主要说了司法和新闻媒体在今天这样一个形成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条件下它们的重要性,那么如何建立呢?
陈志武:相对来说,新闻媒体与前二十年比,其制度建设要走得好一些,程度要比司法改革快多了。
问:您指的程度是什么?
陈志武:制度建设。指的是媒体有什么不同声音时,并没有以前那么多的打压。
问:这是制度建设吗?
陈志武:制度建设包括两方面,一种是有形的,指成文的书面上的东西,一种是无形的,无形的制度建设比有形的更重要。比如说,以往的学生了解经济都是通过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来实现的,而这门课程中教会我们两个概念,一个是剥削,一个是资本家的残酷,这让许多老百姓对今天的市场化经济有了一个不太好的看法,看到有钱人就想到“剥削”。这说明有形的市场制度建设是一回事,支持市场发展的“无形”观念性制度建设则为另一回事。如果没有后者的话,市场发展的阻力会越来越大。在中国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市场经济学知识的普及却还那么少,还停在三四十年以前的“剥削” 经济学上,这实际上给中国的未来发展埋下了炸弹,这种不稳定因素非常危险。如果老百姓对基本经济学概念只是这样的话,他们一看到市场财富的分配不平均,就会有问题。所以我说无形的制度建设包括整个社会对于每一种有形制度的理解、接受、认同程度,这些太重要了,否则容易产生社会震荡。
问:您是说中国社会比较认同新闻媒体所做的一些事情?
陈志武:人们对开放新闻媒体的认同度还是有的。现在中国新闻法还没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新闻法没出来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因为反而可能给新闻界、法律界一些创新的空间。
问:哪种意义上说呢?
陈志武:这要看是什么样的新闻法,如果是约束性的新闻法反而不好。两年前我收集了两百多个涉及有关媒体诉讼的案例,其实通过研究这些案例,与新闻有关的诉讼中,从2001年到现在,法官判媒体侵权的频率越来越低,这表明整个社会对媒体自由的心理接受程度越来越大,理解程度也越来越深。这里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判决媒体败诉时法官给媒体的处罚在逐年加重,我从中感到的是人们对不负责任滥用新闻自由,对不负责的人也越来越反感。我说的媒体无形的制度建设就是指这些方面,指的是社会对新闻自由的认同的深化。
问:在司法这方面,无形的制度建设呢?
陈志武:这些年通过的法律很多很多,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与我们现在通过的法律数量相比。但相比之下,其无形的法治建设却不那么令人满意。
问:怎么判断不那么好呢?
陈志武:就是人们的法治意识在许多方面还不是很强,其中政治方面的原因以及文化传统方面原因都有。
问:那么美国在司法这方面有形的制度和无形的制度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陈志武:用搞法学研究的话说,最好的法治是一般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不要去感觉法律的存在但照样不违法,法律要是与社会大多数人的习惯做法或基本价值观相违背时,那种法律也实现不了,其执行成本也会太大,使法律的尊严受损。比如,在美国社会中,商业交易合同每天千千万万,但是如果你做一个调查看每天签署的每100个合约中最后需要到法院里去解决的有多少,你会发现那远远低于1%。这说明人们的无形的观念对有形的法制的理解是比较深入的。这样整个社会才会有效地运转起来,不会觉得为了法治执行而带给社会的成本太高。
问:您看中国司法界有哪些还需加强的呢?
陈志武:如果与有关国营与民营的讨论联系在一起或许更能说明问题。
二
问:国营、民营跟法治有什么关系?
陈志武:如果要在国企与民营中选择的话,毫无疑问民营是最好的选择,在人类历史文明史上,你去看看哪些国家是靠国营做起来的,几乎是没有的。国营主要是19世纪末,尤其是“二战”以后才在世界范围内做了一个大的实验。这个实验主要在前苏联和东欧等地区开始,然后扩展到亚非拉,甚至西欧。如果一个行业有一两个大的国家企业在其中的话,那么这个行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化发展,不可能给民间任何创业的空间,那个行业也不可能有好的法治。我们在政治学中就讲,什么叫国家,有一个定义是,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地使用暴力的组织。你如果在整个行业中有1 000个企业,其中一个是国家控股的,其余的全部是民营的,那么,这些民营企业根本上无法与这个国有企业竞争,也根本不能是一个层面上的竞争。因为国有企业的主要老板是国家,而国家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国家也运作着法院司法系统,你说那个行业里怎么能有真正的公平、平等的法治?有了国有企业这种“特权超级公司”,“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就难以行得通,司法也不可能独立。
问:暴力是什么意思?
陈志武:我今天说这个桌子是一万元才可以卖,如果谁家私营企业要以500元的价格出售的话,我就要求我的大股东政府关掉你。所以,你也就得选择一万元出售,不能跟我竞争。
问:今天的市场不是您所说的这种市场,我们看不到这样的行为发生,这也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陈志武:这是比较极端的,但如果真要用这个权力,那是没问题的。你很难说中国的汽油行业今天不是这样,本来有许多民间加油站,但中石油、中石化通过政府把许多民间加油变为“非法”了,这类例子还是很多。几乎在所有的国家都不应该有国有的企业在竞争性领域中存在。其实暴力以外,国家还有立法的权力,还可用法规的形式来排挤竞争。
问:照您这样一个说法,几乎在任何一个竞争性领域都不能有国有企业存在,那么美国是这样一个情形吗?
陈志武:在美国即使是高速公路、公园、监狱等许多都是以合约的形式给民营来经营。
问:那么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会是这样一种状况吗?
陈志武:现在很多国家照样有国家持股现象,从静态看是这样的。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至少有一百多个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民营化,我们可能以为除了东欧和前苏联进行了这种大规模的私有化外没有其他国家这样做,其实不是这样,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朝着市场化方向进行,私有化所涉及的数量和进程真的让人佩服,每个国家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都作了一系列朝着民营化方向的改革,之所以有130多个国家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搞国营,那么国家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则的执行者,同时又是经济利益的参与者。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民间的空间还有多少?从经济学和法学理论所讲到的利益回避原则讲这都是讲不通的。
问:您知道中国过去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前进也不过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的国家,真正算起来还不到,其实直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也就是1994年中国才确立市场经济为主体的改革方向,这样算也就只有10年的时间,要在10年的时间内,将所有的国有企业全部退出竞争领域,可能需要一个过程,所谓“国退民进”的思路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但需要时间。但是谈到这里我也有一个疑问,俄罗斯,它的私有化的程度应该说不小,但是现在,在这个国家各个领域的良性竞争状况出现了吗?当我们看不到一个好的结果时,我们向前走的步子是不是要更加小心呢?
陈志武:关于俄罗斯的经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里有许多误解。
问:在中国信息产业,四大巨头全是国有,按照您的理论,您说这个产业如何发展?
陈志武:最近有一个荒唐的讨论,有些人说四要合二,原因是电信产业是竞争太激烈,浪费太多。我想这真是一个笑话,这些人稍微了解一下电信领域的利润有多高,他们就应该知道这个行业不仅不能合二,而且应进一步放开。比如我,我宁愿回到美国向中国打电话,而不愿意在中国用手机打国内的电话,因为在中国国内的人之间打电话是六角一分钟,在美国向中国打是每分钟四美分,三角多钱人民币,比国内便宜一半。你说这好笑吗,其实,最后这些电信利润都是由消费者提供的垄断利润。
问:这个公司是国家的,那么利润给国家,税收给国家,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陈志武:有没有想到为腐败也提供了物质基础空间?
问:如果你是中国电信领域的任何一个老总,您会来这样分析问题吗?
陈志武:那不会。
问: 那又会说出一套什么样的话呢?
陈志武:我就会竭力说服国家发改委和其他的政府部门以及媒体,会说中国电信行业的竞争太激烈,浪费太多,同时说这件事时自己也会告诉自己,竞争也让我太辛苦。因为谁愿意面对这些竞争呢,多休息一会儿,多一些利润在我这儿不好吗?
问:这倒是很有意思。
陈志武:从他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来说,他只能这么讲,他如果不这么讲就应该被换掉。为了股东的利益他即使有什么别的想法也不能讲出来。
问:他在做着这些事情时会不会能有一个声音告诉他,现在所做是与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相逆的,会吗?
陈志武:不会,他并不是救世主,也不应该是,他必须使他的利益最大化,他必须站在他的利益群体上,我们也不能以别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他。
三
问:经济学家总是以利益的角度来看社会,这是不是有一些失之偏颇?中国人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角度来评价许多事物。是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角度在主导着社会的评价?而在发展中国家人们更多地用伦理道德来评价。
陈志武:对,美国社会中利益的评价是很常见的。
问:中国社会则不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好恶都是与伦理道德相关的。
陈志武:说到伦理,最近几个月在由郎咸平引发的争论中,不断在我头脑中回旋着的一句话是“往事不堪回首”,还有一句叫“往事并不如烟”。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不发达的社会带给人们的痛苦……其实像我这样的人相对来说比较超脱一些,从生活上来讲,我除了教学,自己也有对冲基金公司,当然我不是那么暴富,但还可以。最近我带着很大的好奇心去了解究竟国有企业是如何起源的,在中国历史上是什么原因让一些人头脑发热。当初的国有化过程远比今天私有化的过程要不公平得多。今天有一些人对私有化给许多人提供的暴富的机会抱不平,这当然对,可是当初有多少人家经过多少代人积累的财产也一下子变为公有。个人拥有财产、拥有私人的产权实在太重要了,当一个人一无所有,没有起码的经济保证时,其他什么权利、什么尊严也谈不上,你无法有争取自己权利的底基,为了生存和家庭,你只好任别人摆布。当你拥有一些自己的财产时,你就有自己的独立性,你就能自主。正因为当初前苏联的国有化是很残忍的,那么今天的私有化的过程也会让一些人、一些家庭付出一些代价,因为在过去国有化的大玩笑后,我们再折腾一次几乎没有无震荡的解决方案。所以今天市场化过程中有许多的问题要历史地看,而且是必须经历的,是人们重获自主权的必经之路。
你说的俄罗斯,多数公司留下40%股份给员工,还有一些是给当地人,其他分给全国老百姓,很平均。人均一份并不是经济效率很高的安排,因为人生来权利平等但能力并不可能平等,市场经济中最有能力的人掌握的资源会最多,给社会的贡献可能也最大。其实俄罗斯的经济改革起步很晚,这几年它的经济增长率也是比较稳健的,所以,很难说俄罗斯的不改革如中国的改革方式。
问:那您是怎么评价的?
陈志武:从我讲的制度资本的角度看,它这一方面提供的潜力很大,中国社会今天还有一些非常大的宏观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将许多年的努力成果付之一炬。话又说回来,很多人不知道当年前苏联从1928年开始进行的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后来有二十几年的快速增长时间,当时前苏联的GDP年增长是12%,13%,所以后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到底是市场经济好还是国有经济好的争论,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它们认为前苏联为它们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示范,但后来发现历史是开了一个大的玩笑。所以说现在很快地下一个结论说俄罗斯如何,结论可能还暂时过早。当然,我希望中国社会不要经过太多的震动。
问:我认为你说的制度化建设对中国当前的情况在许多的领域是非常有价值的,其实有许多人也看到了,但认识没有如此深切。
陈志武:对,制度化的建设对于长治久安来说太重要了。
问:你在说到新闻媒体制度化建设时,常常只提财经领域,这很有意思,在中国经济与其他领域几乎是一体的。
陈志武:这完全是由于中国今天的特定环境来作的一个选择。正因为特定的环境帮了我一个忙,我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新闻媒体的作用。
四
问:当很多人提到中国和美国的区别时,人们总是说到美国更重视个人主义,而中国更重视集体主义。
陈志武:实际上在中国你不强调集体主义还不行。因为金融证券不发达,个人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证券这样的经济基础,人们不得不靠家族、宗族、靠社会来代替金融证券应该发挥的作用。一个人的一辈子中有四种风险很重要,一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事件,比如天灾人祸,发生这些小概率事件时你就需要帮助,也就是对保险的需求,你需要医疗保险、天灾保险、财产保险(如房屋险、火险)、汽车保险等。第二是一次性的大的开支,比如,盖房、娶媳妇嫁女、买车等,因为这些会给自己的经济和财力有很大但是一次性的冲击,你就需要借贷。这两种是最基本的。第三是养老。第四是投资创业。我所说的个人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是因为没有这四大块金融与证券业的支撑,你就不得不靠家族,靠某种集体来起到保险、借贷、养老和创业融资的作用,也就是说,家族与集体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合作体。在没有发达的正式保险业、借贷业、养老基金业和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你就无法离开家族与集体这种替代性的非正式的金融组织。所以我们会看到,在中国农村是靠养子防老,靠后代和亲戚来规避一个人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问:这种东西的维系是靠伦理道德来起作用的。
陈志武:我是说只有在金融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为很强的个人主义文化提供条件,那时个人主义才可行。
问:中国今天的金融市场并不是很发达,但个人主义在中国城市发展得还不错。
陈志武:现在大多数的中国社会里还是不行,因为在城市有自己的财产、有保险、有养老金等,所以在城市里人们可以不再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自己对未来的投资,对未来的保险。这是中国农村和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不同程度决定了这种观念的不同。中国文化《三字经》中的“父母在,不远游”,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如果我的子女跑到纽约去了,离我这么远,那我的投资怎么办呢?那我的养老金怎么办呢?我的医疗保险呢?为了保证父辈在后代身上的投资,在家族里的投资能有所回报,从投资者权益保护的角度讲,你就必须有一套保护父辈作为投资者的权益的制度架构,否则你老了之后或病倒之后就无依无靠了。而传统中国不强调正式司法,那么只能靠道德伦理来保护,道德伦理发挥作用的方式是靠内疚心理来完成,而不是靠外部制度来保障。因此,你在儿子还小的时候就必须给他灌输很多家庭道德观念,强调光宗耀祖,让他在不听你话时、在不孝时、在不义时都能深感内疚,最好是让他自发内疚得不能自己,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你在他身上的投资是否可靠了,你的养老、保险也可能都有了。因此,许多制度性文化是社会内生的,是随着经济活动的变化而变的,同时文化又反过来约束或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是几千年维系下来的,说明它有多厉害。其实,维系几千年不奇怪,因为过去几千年里在交通与通信上没有太大的变革,没有火车、汽车、飞机、电报、电话等技术变革对社会产生的变迁这么大,那时候的经济活动范围也很小,传统的文化当然能维系几千年。
问:可是这样子女就很难走远,当一代又一代的人这么要求后代时,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代都不会将自己个体的生命价值发挥最大。很有意思,这样来看,您这是关于个体与群体的差别的一种解释。
陈志武:这样,每一代达到的效率都会打折扣,每一代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潜能。所以说,有了金融的手段后,就让每一个人的潜能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为什么美国这类国家的生产率那么高呢?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问:我特想问您,美国在金融发展之前,它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是个什么情景?
陈志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在1800年左右,几乎都在从事农业。今天,现代化程度高了之后,农业人口只占2%。有人认为美国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所以给美国带来那么大的冲击,原因是到19世纪中期美国还是一个较为传统的社会,那个时候金融还不发达,绝大多数美国的家庭都居住在附近,还是以家族里的家庭之间互相提供经济上的担保来维持发展的。从1850年到1930年这期间,美国的工业化使得人口流动加大,加大后,原先美国人所依赖的家族互助在地理范围上等各个方面都显得越来越难,互助效率也不够,那时的保险、信贷和社保都没有跟上,这两个东西的脱节使得1930年经济大萧条后的人们应付经济危机的能力基本上很弱,所以,为什么那次大萧条会给美国社会带来那么大的冲击,这是其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后来为什么罗斯福在1933年、1934年、1935年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以提供社会需要的各种保障呢?因为这是社会所能提供给人们的最后的一个保障。后来的金融发展可以看成是美国社会对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的一种必要的回应。
问:社会人口流动加大后,带给社会结构的根本性的改变可能来得太猛,这就像中国两个多亿的农民工进城一样,社会大规模群体的流动后,其相应的各种制度必须跟上,否则就会带来许多连锁反应,比如,农民的工钱讨不回来,教育问题等一系列的问题。
陈志武:这就是我所说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这也是当今中国跟昔日中国的根本性差别。
问:谈到这里我有一个不同的观点,您刚才说是金融带给社会个性化发展的空间和可能性,但我认为金融是一个结果,而不是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个性化的浪潮是由于工业化革命带来的。工业化浪潮打破了原先的社会结构。
陈志武:对,打乱了以后,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东西解体了,这样需要金融跟上,后来工业化的扩大,就更加带动了外部金融市场的发展。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美国的金融发展,其个人主义则不太可能。
问:在这里我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就缺少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工业化的进程,我曾经到过日本的农村,工业化的程度已经在每个家门前都能看到。其实发达国家都经过了工业文明的洗礼,这个洗礼带给社会的改革除了金融的发达以外,还有一种文化习惯,比如程序化,法治化,这些东西与工业化都是相关联的。为什么今天您所说的无形的制度建设在司法领域很难,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当人们更多的相信权力不是相信法律时,从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官本位的残余观念在中国的势力,这种东西没有通过大范围的工业化的浪潮冲击,非常难以消失。
陈志武:有道理。
问:现在,中国倒是有一个大的流动,这种流动就是我们所说的农民工进城,全国范围内有二个多亿的人在向城市流动,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没有过的现象,尤其是如此的大规模,刚刚改革开放到现在也有一个群体流动过,这个群体在二十多年中有58万,这就是出国人员,这群人对中国社会的改变其实很大,有些改变只有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看到。但这个群体的规模比起农民工来说太小了,所以我想,如果有谁关注农民工进城后带给中国社会的改变,这是很大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题目。但这个与工业化浪潮相比还是不太相同,因为没有在中国整个范围内铺开。
陈志武:其实这种流动带给社会的变化我已经看到了许多。有很多是体现在细节上的,要细心地观察才能体会到。
问:在这样的大群体流动后,其实很多原先的东西打破了,但问题是,打破之后新的东西并未建立。
陈志武:农村很多的原先维系的东西慢慢没有了。
问:我在这里又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发展与现在发达国家相比,拉下了一个历史阶段,就是工业文明,所以在中国这样一个起点与发达国家并不一样的社会中要进行您所说的私有化的进程,是否合适也需要打上一个问号?这个就是所谓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大的特色。
陈志武:其实,不存在美国人与中国人的差别,只是因为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和制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来我们今天看到的局面。这些都是后天的,人为的,这种差别不是人本质上的差别。因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价值观是不太一样的。其实就在中国西部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相差也很大。私有化不是问题,因为人类历史上最原始的、维系最久的形式就是私有制度,企业的组织形式最久、最老的也是私有制。因为这是最接近人性的,这个道理适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