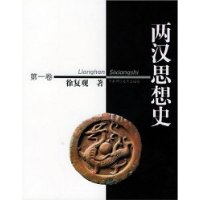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页码:1051 页
出版日期:2004年02月
ISBN:7561728166
条形码:9787561728161
版本:第1版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套装数量:3
内容简介 《两汉思想史》三卷是徐先生于上一世纪70年代陆续出版的代表性巨著,那时他已是七十岁的人了。第一卷原名《周秦汉政治社会结构之研究》,是《两汉思想史》的背景篇,后两卷是正篇。
徐著《两汉思想史》的鲜明特点是:
第一,通过对周秦汉,特别是汉代社会政治结构的探讨,深刻揭露、鞭笞了专制政治。徐先生着力检讨中国传统政治,批判一人专制。在《封建政治社会的崩溃及典型专制政治的成立》、《汉代专制政治下的封建问题》、《汉代一人专制政治下的官制演变》等长篇专论中,徐先生从制度上详考了中国专制政体的形成与演变,分析了宰相制度被破坏的过程,不仅指出“家天下的法制化”的弊病,而且刻划了专制者的心理状态。他说:“一人专制者的心理,即使是自己所建立、所承认的客观性的官制乃至任何制度,皆可由他一时的便宜而弃之如遗。”“一人专制,需要有人分担他的权力,但又最害怕有人分担他的权力。这便使宰相首遭其殃。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由一人专制自然而然所产生的狂妄心理,以为自己的地位既是君临于兆民之上,便幻想着自己的才智也是超出于兆人之上。这种无可伦比地才智自我陶醉的幻想,便要求他突破一切制度的限制,作直接地自我表现。”(第一卷,第153页。)当然,在我们看来,专制者的心理是其次的,决定政冶结构的关键尚不在此。政治、经济资源配制的状况,军事的压力,财产与权力分配与再分配的成本和效益的问题,是制度建构与政治架构修正的主要原因。
钱穆(宾四)先生对汉代政治的描述与评价(请见《国史大纲》),与徐先生大相径庭。钱穆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指出汉代政治是文士政治,非专制政治,在制度建设上奠定了中国政治的格局,其成就大于负面。按钱穆的看法,秦汉以降,中国传统社会使平民通过教育可以参与政治的机制,特别是有“考试”与“铨选”制度为维持政治纪纲的两大骨干,沟通社会与政府,则不可以对两千年历史一言以蔽之曰“专制”、“黑暗”。徐先生曾经老实不客气地著文批判钱先生是“良知的迷惘”。徐指出他自己“所发掘的却是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缓和专制,在专制中注入若干开明因素,在专制下如何多保持一线民族生机的圣贤之心、隐逸之节,伟大史学家文学家面对人民的鸣咽呻吟,及志士仁人忠臣义士,在专制中所流的血与泪。”(徐文见台湾《华冈学报》1979年第8期)
徐钱间的公案今且不表,由是大概可以知道徐氏是一位情感奔放的学者。读《两汉思想史》,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他的民主政治的情意结。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指出,秦汉至清末,以君道为中心,“专制政体理论之精确完备,世未有逾中国者。”(见萧著下册,第947页)按萧公权的看法,这二千余年,中国政治体制和政治思想“多因袭而少创造”。而徐复观先生则充分论证了周室宗法封建解体的原因、过程与秦汉专制政体的形成演变问题,乃至中国姓氏的演变与社会结构、专制政治与宗族的关系等。请注意,徐先生使用的“封建”概念是准确的,是中国古代的原始涵义,而我们现在习见的“封建社会”概念是不准确的,是西方史的涵义,类似于徐著中的“专制政治”的意思。
第二,与上一个问题有关,徐著特别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第一卷有《西汉知识分子对专制政治的压力感》的专论,第二卷有关《吕氏春秋》、陆贾、贾谊、《淮南子》与刘安、董仲舒、扬雄、王充等思想的论述,第三卷有关《韩诗外传》中士的立身处世和“士节”的强调,及有关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表现的史学精神与目的的论述,都涉及到知识分子问题。徐先生说:“若不能首先把握到两汉知识分子的这种压力感,便等于不了解两汉的知识分子。若不对这种压力感的根源——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及在此种政治下的社会作一确切的解析、透视,则两汉知识分子的行为与言论,将成为脱离了时间空间的飘浮无根之物,不可能看出它有任何确切意义。”(第一卷,第167页)西汉知识分子为什么反秦?反秦实际上即是反汉。为什么喜欢《离骚》?那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的处境与心境之自况。司马迁的“意有所郁结”的感愤之作,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等等,都是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对命运、遭际的情感抒发。
在第三卷《原始——由宗教通向人文的史学的成立》这一专论中,徐先生不仅考察了“史”的原始职务,与祝、卜、巫的关系,尤其论述了史职由宗教向人文的演进,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的交融。优秀的史官,实际上正是以“代天行道”的宗教精神来执行他的庄严任务的。这就是一种“书法”。孔子赞扬的“古之良史”董狐和为了写出“崔杼弑其君”而牺牲的兄弟三史官及前仆后继的史官即是明证。徐先生说:“这不是西方‘爱智’的传统所能解释的。因为他们感到站在自己职务上,代替神来做一种庄严的审判,值得投下自己的生命。”(第三卷,第143页)全书对汉代优秀知识分子以理想指导、批判现实政治的研究,甚有独到之见。这也使我们很自然地想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入世关怀、政治参与和不绝如缕的牺牲精神。
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以价值理念指导、提升社会政治。请读者读一读本书二卷《刘向<新序>、<说苑>的研究》第五节有关刘向针对现实政治、突破现实政治的理想性的讨论和第六节“以士为中心的各种问题”以及《贾谊思想的再发现》第五节“贾谊政治思想中的现实性与理想性”。从这里可知儒家政治理念的功能和儒家政治思想不同于、高于法家政治思想的缘由。“以民为本,以民为命,以民为功,以民为力,一切过失,都由君与吏负责,决不能诿之于民。”(第二卷,第85页)徐先生特别肯定“政治以人民为主”的观点,又善于发掘传统政治思想的资源,没有陷于今天自诩为“自由主义者”的某些人的浅薄与狂妄。
第三,学术上的贡献与严谨的学风。徐先生的《两汉思想史》反映了作者的创慧。在他以前,很少有人注意到《新序》、《说苑》中引用孔子的材料在比例上超过了《韩诗外传》的问题。这一问题,随着今天大量出土简帛的出现得到照应。我们很遗憾,徐先生写作本书时,只略为了解了一点点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尚不可能知道帛书《易传》及儒家与诸子百家的帛书资料,更不可能知道90年代郭店楚简与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中大量丰富的思想史资料。实际上,孔门七十子后学记述、传衍的大量资料,在汉代典籍中得到保留,除前述刘向所编书外,尚有陆贾《新语》、贾谊《新书》,乃至《吕览》、《淮南》等。地下发掘的竹帛与传统文献对比,诸如《诗》《书》传衍世系与家派,诗教、书教、礼教与乐教,思孟“五行”,先秦两汉心性论问题,都有了更丰富的材料,而超出于陈说。我们特别注意到,徐先生在没有获悉这些新材料时,由于他苦心研读文献,而有了突破前人的慧识己见。他超越了“疑古派”,依据自己的考据工夫,把“五四”以来认为不可信赖的文献重新加以定位,大胆地加以证实与运用。举凡有关汉代思想史上的大家和重要典籍,他都有讨论且都有独到的见解而不肯阿附陈说。他尤其重视孔子人文精神在两汉的巨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学的问题,礼乐的问题,天、命、性、道、身、心、情、才等人性论问题的展开等。又如他说,《吕氏春秋》最要者是《十二纪》纪首,其中积淀了汉代以前的宇宙——世界观,又规定了影响了两汉学术与政治。他认为,董仲舒成就的“天”的哲学大系统是当时专制政治趋于成熟的表现,但董氏仍然持守儒家政治理念,批判现实政治,力求限制专制之主及其酷烈的刑法。
从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作者严谨扎实的学风,他的研究建立在第一手基本资料的考证、解释、批评上,他有识见,有眼光,他坚决反对浮光掠影、投机取巧。这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尤有意义。
媒体推荐 书评
徐复观所著《两汉思想史》,是近年来有关两汉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论著。徐氏这部书有两点最值得称道的优点:一是他的观点和纲维,都是出于自己读书和思考的心得;二是在史料方面下过一番考证的工夫。所以读者尽管可以不同意他的议论,但他的这些优点却值得重视和效法的。
目录
两汉思想史(第一卷)
三版改名自序
有关中国殷周社会性格问题的补充意见台湾版代序
自序
西周政治社会的结构性格问题
一、对西周奴隶社会论者的检讨
……
文摘 书摘
……有关同样性质的金文材料很多,这里只简抄西周奴隶社会论者所应用得较多的若干例子。在西周奴隶社会论者中,大概可分为两型:一型以郭沫若为代表,认为当时奴隶之范围甚大,上引金文材料中,凡被“锡”与之人,皆是奴隶。“人鬲”是奴隶,“庶人乃人鬲中之最下一等”,《矢》中之“王人”、“甸人”与“氓”,也是奴隶。如郭氏之说,则西周诚不愧为奴隶社会。另一型则认当时奴隶之范围较小,姑以杨宽为代表。不以“庶人”为奴隶,而以“人鬲”、“丑”、“讯”、“臣”及手工业之百工等为奴隶,其来源皆为战争之俘虏。并还有“部族奴隶”。在上述两型主张中,有一共同之点,即是都引《诗经周颂载芟》上的“千耦其耘”,及《周颂噫嘻》的“十千维耦”的诗,以作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证明。因为他们认为若非使用奴隶以从事于农业,便不会有这样大规模的劳动。
由金文研究,可以补证典册记载之所不足,诚为治古史者所必须之工作。然“周时文字,点画自由,略无定律”。以金文中之文字为尤甚。故对金文之解读,必以在典册中可以得到互证旁证者为能近于真实。又其文字简质,在解释时若无典册上之互证旁证,即不应随意加以联想扩充。
按古代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由战争所得的俘虏,这是历史的事实。西周有战争,西周便有俘虏,便有由俘虏而来的奴隶,这是无可置疑的。《尚书牧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这很显明地指出了俘虏的用途。但“人鬲”、“鬲’,是否即由俘虏而来的奴隶,便非常可疑。“鬲”是鼎属的器具,在典册中丝毫找不出是俘虏、奴隶的痕迹。且幅尊》:“鬲锡贝于王。”鬲在此处是人名,其非奴隶,甚为显著。绝对多数的金文学者,都以鬲为“献”之省。“人鬲”即“民献”或。“献民”。于是李剑农即以人献为奴隶。但《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洛浩》:“其大停典殷献民。”(逸周书商誓》:“及百官里居献民”,“天王其有命尔百姓献民”,《度邑》:“九牧之师,见王于殷郊,乃征厥献民”,《作洛》“俘虏献民,迁于九毕”。被俘而迁于九毕的殷献民可能成为奴隶;但献民之本义乃指人民中持有才能者而言,无法解释为奴隶。于是有人主张‘嗝”即是《逸周书世俘篇》的“磨”,由此以证明其为由俘虏而来的奴隶,这从文字训诂的观点说,未免太牵强了⑤。最低限度,此说是非常可疑的。即使承认此一说法,其人数也不足以构成一个“奴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