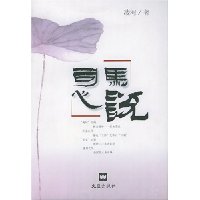
基本信息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页码:718 页
出版日期:2002年01月
ISBN:7806761152
条形码:9787806761151
版本:增订版
装帧:平装
开本:32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司马心说》作者凌河,为沪上知名评论家和杂文家,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曾七次荣获中国新闻奖和上海新闻奖的一等奖,现为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已发表社评、论文、时评、杂文数千篇,尤其是以“司马心”为笔名撰写的杂文和时评,以其敏锐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和犀利幽默的文风受到读者的欢迎。本书选编的600余篇杂文时评,涉及政治、经济、思想、道德、文化、军事、国际、科技、体育等众多领域,不但具有关注时世变革、倡言观念更新、针砭时弊积习、痛斥不正之风的特点,更显现出作者对于社会根源、文化背景、道德传统、国民性格特征的开掘和剖析,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较深的思想涵义。
本书还首次全文收入了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于《解放日报》并引起巨大反响的“皇甫平”系统评论。凌河是这组系列评论的作者之一。
作者简介 司马心,名凌河,一九五二年秋生于上海,浙江湖州人。曾任律师。现任解放日报评论部主任。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及五次上海新闻奖一等奖,膺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称号。发表社评、政论、杂文、随笔数千篇,著有《世风别裁》、《世相百态》、《大风集》、《高鼻子的阿Q》、《司马心说》等专集。撰发《论中国封建官僚制度》、《论贝卡利亚的刑罚价值体系》等长篇论文,主编《中国当代人文思潮》法学卷、《公民法律手册》等。
媒体推荐 关于杂文之宣言(代序)
若要给杂文征集宣言,“针砭时弊”四字,大概是人人不会忘却的。事情也确是如此,尽管“匕首和投枪”的说法不太时兴了,然而弊端却时时可见,杂文的版面,当然便不能挪作清谈的茶馆、遁世的净土。如果空有机敏的谈锋或是奇俏的借喻,而超尘脱俗,而山水风光,杂文家的“社会责任心”,恐怕就要为人所怀疑了。
然而需要针砭的时弊,却并非总是一“时”才起;而必须声讨“之的”,竟也往往与“众矢”们不无关系。举“弊”大者,例如那场浩劫,针砭了十年,才知源远流长,其弊竟深植于“悠悠文明”之中,才知其剧之悲,恐怕值得人人反思。于是巴金先生写五卷《随想录》,剖心自省;而更多的我辈,恐怕连“违心”都算不上,只是“忘情”而已。只是不少杂文高手,在“针砭时弊”之时,常常怒目远视,而屡屡忘记了身边的受害者,身上的受害处。此种情况,当然远非只是针砭“文革”时方才发生。
于是杂文家便容易受到公众拥戴,因为如此“针砭”,不但骁勇痛快之至,而且常常使读杂文的百千万人,围观“一弊”受诛而抚掌大笑,是为“出了口气”。而“出气”之后,则仍然回去祭灶君、贴门神,而后慢慢地洗脸,稳稳地睡觉。这种热闹,在中国不但算作一种“时弊”,而且简直是一种“国粹”。而若使这百千万人(包括杂文家在内),反躬自问,扪心自省,说是此一“弊”之存,竟与芸芸众生大大有关,例如官僚主义严重之处,莫不是民主“不言”之地;例如流言杀人之事,莫不因街传巷议之故,因此“气”似应且慢“出”,留着渐渐地荡回,该种“针砭”,恐怕算得更为“切中”了。
在谈及中国当代文学之社会责任时,一位相当有名的作家告诉我:剖析和瓦解一种旧文化,其作用决不比揭露一二个“特权”小。我认为这位作家对于时弊的看法,“针砭”到了文化背景的深层;作为文学的杂文,当属形象思维的一类,恐怕还须让读者从这形象里看到自己,进而从自己身上看出“杂文”来。例如鲁迅先生写未庄之事,并非只是针砭赵太爷之“时弊”,而一个受苦受难的阿Q,反倒呼之欲出,令人悲怒,发人自省,助人自胜,催人自强,及至今世,仍在促人去制订发展文化之战略。若只是满足于“让百姓出气”,或仅仅得趣于让“众看官”围观一番后,觉得“声讨”、“诛之”既罢,乾坤业已朗朗,而文化一仍旧章,流弊不时复辟,“国民之性”依然,老谱世代相袭,那么,杂文作为文学的社会认识价值,大概就不会与杂文家“唤起民众”的社会责任相称了。
目录
关于杂文之宣言(代序)
“下”之不“能”
“靠站吃站”与“靠权吃权”
藤泽削发
“社会效果”议
……
文摘 书摘
中国文学国际讨论会在金山举行的时候,我是去了的。这次会议,有许多轰动的新闻,然而最使我“有感”的,却是马悦然先生的“遭遇”。
那次到金山之前,马悦然先生是有言在先的。这位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大评委,把中国文学的长期无缘于诺贝尔,归结于翻译方面,作为权威的汉学家,他以为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内在价值的介绍,还处于相当外观的程度,尤其是对产生作品的那个文化环境,“翻译”甚难准确。然而到了金山,马悦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一位中国大作家来一番客套之后,直言马悦然对某些中国作家颇有“偏爱”;接着苏联汉学家的机敏反诘,则涉及到意识形态的分歧;而英国语系一位学者,竟建议马悦然转告诺贝尔奖评委们,检讨对东西方文化的“基本态度”……好一个“群儒舌战”,竟使我们在座的不少记者加上一位素以“勇敢”著称的中国新潮作家深为担心——如此围攻,人家何以吃得消?是否应向主席台暗递一条,建议将“舌战”引向他方?对这位颇有分量的国际友人,难道就不需动用“统战政策”加以保护,听凭张昭、顾雍们出言不逊地围着不放,闹得我们旁观的人也觉得脸红?
那次“围攻”之后,一位中国记者在走廊上碰到马悦然先生,竟有了莫名其妙的歉意,并慰问先生是否吃得消?不料马悦然大惑之下,竟不解这“局促不安”的来由。他当然是明白“吃不消”的意思的,所以答曰:宽容不是礼让,只是让各人自由发表不同意见……
其实我们中国人,曾是以斗争哲学著称于世的,在过去的年月中,我们似乎很少对无休止的斗争表示过“莫名其妙的歉意”;那无处不在的“窝里斗”,不也未曾使我们自觉“丑陋”吗?不知为何,碰上了“各人自由发表不同意见”,反而变得紧张、腼腆、“局促不安”了。不要说是亲自参加“舌战”,便是旁观一番,也竟会觉得“看不下去”的。这部分“文化”的内在价值,恐怕连马悦然这样的权威汉学家,也会难以“翻译”得准确。
所以我想,我们身上的“传统”真是扑朔迷离。曾经请熟过“斗则进”的民族,为什么反而羞怯于堂堂正正的“争鸣”?十年里三缄其口苦不堪言的人们,到了可以说话时,为什么反而对自由的言语“听不进去”了呢?至于“一言”既逝,满堂反而无声;“一锤”方去,百乐顿觉惶然不知所以的事儿,就更值得深重地“反思”了。外加的专制,在中国已经正寝,而内心深层的“传统”,却仍“专制”着我们的思想,怎么也难以宽松。我们中国人,不应当赶快走出这重重的自缚之茧,这种种自我
……